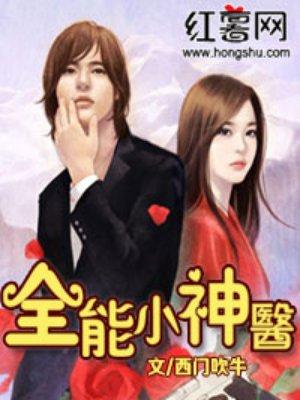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69章(第3页)
那个凶狠的海上老大手持一根棍子,不停地巡视,拉鱼的人稍有懈怠,就要被他连踢带打一顿怒斥。有一次他用手中的棍子压了压父亲的拽绳,嫌它不紧,就立刻把父亲掀翻在地。父亲在炙人的沙子上滚动、躲闪,海上老大就不停地踢他。踢啊踢啊,海上老大就像踢那些年轻人一样,踢得父亲最后蜷到了一起。父亲两手拼命护住身子一侧时,我突然想起了父亲以前断过两根肋骨。那个河边的罪孽感又一次淹没了我。与此同时,我更加明白了妈妈为什么让我跟了来,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下面生的一切都让对方猝不及防。我呼喊着扑过去,那一刻肯定像个狰狞的小兽。
海上老大一时呆住了。
父亲趁机爬起,却用严厉的目光阻止我……
我一切都视而不见。我狠狠地抱住了海上老大一双又沉又重的、下端陷入沙子的腿,想把他一下顶翻。可是我这才现太难了,这双腿就像两根石柱子。海上老大低头看我,目光里满是怜悯。可是这就越激怒了我。我再次掀动了两下,然后就动用了牙齿。海上老大脸上的怜悯没有了,很快啊啊大叫,跳着,挣脱着。可是我紧紧咬住了他……我记得海上老大像狼一样嚎着,直到有人赶过来把我们俩分开。
我大口喘息,揩着一脸的沙子和汗,还有血——这是海上老大的血。父亲在一边踞着。海上老大一会儿出一声尖叫,一阵怒骂,还想将扶住他的人推开。我听到了大家劝慰的声音。就在这时,我看到父亲缓缓站起来,捡起了一边的那根属于海上老大的棍子,一步步向我走来。我不相信他会打我,我只是盯着他。
他艰难地走近了,举起棍子。
棍子举得很高,一下下落在我的屁股上。我全忍受了。
回家后母亲掀开我的裤子看了看,没有现红肿的地方。“痛不痛?”我摇摇头,“你当时为什么不跑呢?”我摇摇头。
我和梅子登上一座沙岭。大海仿佛就在眼前。海边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更没有船的影子。海浪疲倦地扑打沙岸。显而易见,海里已经没有鱼了,被污染的水中只有少量贝类。鸥鸟也见不到了,而过去它们总是一群群起落……我们沿着海岸往西,一直走到芦青河湾。
芦青河奔流的水今天已经成了酱『色』。河湾两旁密密的丛林不见了,而是一片片生满了苇荻的水洼……梅子定定地望着河湾。我们都在想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她的父亲。他们都在这儿参加过一场场惨烈的战斗。奇怪的巧合,不可思议的人与历史……
河湾的太阳缓缓降落。
《三张纸币》
一
由于河谷拐了个弯,白天瞄准的群山从这里望去,已经落在河谷的左边。我们沿着山谷走得很慢。这儿的山岭大都由玄武岩构成。脚下的土层很薄,树木长得特别矮小;而生长在河谷里的树木,根须可以深入十几米的地下。所以河谷中的树木总是和山坡上的树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山上瘦小的枝桠在秋天刚刚深入时就脱光了叶子——这使我们想到那些早早谢顶的城里人——我想到了那所地质学院,记得那些在花坛和甬道边缓缓漫步的人大半戴着眼镜,头稀疏,面『色』萎黄……这就是人类当中特殊的一族,他们渐渐都要长成这样一副模样。
随着走下去,我渐渐觉得这一带有些陌生,仿佛从未到过这里似的。可是当我和梅子登上一道山坡的时候,一眼就望见那个小小的村落了——我伸手指着远处那散散落落的棕『色』屋顶,对梅子惊喜地大喊“你看到了吗?你看到它们了吗?”
“就是那个小村吗?”
“对,就是那个小村!”
她满脸兴奋。是啊,她一会儿就要踏上丈夫的滞留之地、那个在一次次叙述中变得多少有些神秘的地方了。我们俩不再耽搁,而且不由得加快了步子,一会儿身上就热汗涔涔……
走进这些石头街巷,我不得不压抑着心中泛起的阵阵激动。奇怪的是,我们进村后已经走了好久,可连一个熟人都没有看见——好像这个村子换了另一茬人,好像完全陌生的一代正在飞长成,他们已经替代和主宰了这里的生活。村里人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和梅子,有时还出两声快意的嬉笑。
他们笑什么?梅子看看我,我也无法回答。
穿过大半个村子,过了村中的一条小河。小河因为在村里转了两个弯,所以我们要两次涉水才能登上村西那个小小的山包山包上有几排平房,它们比村中的房子要高大一些。
梅子这会儿大概知道了我为什么要直奔那里,明白它就是当年那个作坊的旧址——那里有多少故事啊,这里有个叫“偏”的姑娘……
我们涉过河水,登上山包,直接走进了那几排房屋。
房屋阴冷『逼』人,黑苍苍的。岁月没有饶过它们。有几间房屋眼看就要坍塌了,当年筑起的墙壁已经有好几处掉下了墙皮土,『露』出了长长的泥草。几排房子组成了一个院落,院落的大门早就破损了。我一脚踏进去就惊起了一群鸟雀。里面死一样寂静,大概除了老鼠之类再也没有一个活物了。
我屏住呼吸,仔细辨认着,寻觅当年的痕迹。
“就是这儿,这是最北面的几间,当年我们就在这里做夜班。那时候这里多热闹,点起的煤油汽灯照得屋前空地一片通明。里面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秃脑会计的话,我们也许会一直过得快快活活。当时全村的人都眼巴巴地看着这儿,把作坊当成了救星。那时山里人有多么穷,你没法想象。我们每次到外面出差都要借钱凑路费,一个村子的人把钱集中起来,这家三『毛』,那家两『毛』,就带着这些零零散散的钱到外地去……”
梅子一直紧跟在我的后面。我一间一间看得很细,一边走一边给她讲当年的情景。我这会儿感到有点儿奇怪的是,这些房子一直空着,为什么不能派上一点儿用场?它们没人管理,眼看就要全部废掉了。
我在一间屋子跟前迟疑了一会儿,但还是走了进去。
屋里照旧是空空『荡』『荡』。当年的一切都不见了条桌、笨重的木凳、锤子、石板,什么都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是满屋的垃圾,是老鼠扒开的泥土。可是在屋子的一角有一团『乱』草,那上面有人躺过的印迹。梅子也看到了,说“这肯定是那些流浪汉留下来的。”
是的,这片土屋虽然上面『露』着天,已经不成样子了,可它实在还是流浪汉的一个好去处。可是这片土屋让我心里疼,让我紧紧咬住了牙关……
二
我这会儿不愿告诉梅子——不过也许她早就猜到了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有个叫做“偏”的姑娘,有过悲壮骇人的一幕……此刻,在这间黑乎乎的屋子里,惟有她的那双眼睛依旧是那么明亮。它穿过一片时间的雾霭望过来,望着一个满身尘土的人——他归来了,就站在这间屋子里……这儿的声息和气味还是那么清晰可辨,我竟不由自主地伸出了双手,像要抚『摸』什么。到处都是那双沉沉的、带着无限怨艾的女『性』的目光。我在墙上抚『摸』着、辨认着……这儿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岁月把一切都覆盖了。
当我在屋子里细细察看的时候,梅子突然揪住了我的胳膊。我转过脸小窗上好像有人影闪了一下。
“有人……”
梅子点点头。
我们赶紧走出去。真的看到一个人,他正站在窗户旁边,伏在墙上。我刚问了一句,那人迅离开了。
这是一个面『色』黝黑的男人,大约有六十多岁。这个人是谁呢?我觉得他的背影有点儿熟悉,可又实在想不起是谁。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把镰刀。
梅子害怕了。
手握镰刀的黑脸男人站在前边不远处望过来,一声不吭。他只用恶毒的眼睛盯住我,咬着牙齿,眼睛眨也不眨。
正在我疑『惑』的时候,突然他往前闯了一步,胳膊一抖,手里的镰刀掉在了地上。他跑上来,还没等我做出反应,就一下扯住了我。
他嘴里呜呜啰啰喊着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清。
我只想从他的拉扯中挣脱出来……可是这声音多么熟悉!就在即将挣开的一瞬间,我突然想起来了他是偏的哥哥啊!是的,这个男人,就是这个男人……可他怎么会是这样?他在当年是多么强壮的一个小伙子啊,现在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老人,像是一眨眼的工夫变成的!
“是你呀,啊呀你回来了?”他大喊着,张开的大嘴里挺立着几颗残牙。
我告诉他这是梅子,我的妻子——我们已经在大山里走了很久,我们是特意赶来看看当年的作坊的。
我面前的老人肚子疼似的,一下蹲在了地上。他『摸』索着捡起了镰刀。
我真就是个新人
有人告诉江眠这个世界并不普通。尘世之下还有另一个世界,他们称之为域。域中光怪6离,神明被人类屠尽。如果一个游戏高手能够操控角色在现实战斗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我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我是驰骋沙场的将军,我是挥斥方遒的诗人,我是进京赶考的考生,我是卖炭的老翁,我是很多人。我收复与征伐,在天地之中厮杀。即便你是身经百战之人,我真就是个新人...
如此这般的盛世繁华
1983年,改革开放的第五个年头,阳江市一群抱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对未来无限憧憬的人们,开始了各自的奋斗历程,有艰辛与苦难,也有欢乐与祥和。故事平静而又波澜壮阔,叙述了几位主角坎坷而又荡气回肠的人生篇章。如此这般的盛世繁华...
妙手仙医
新出狱的陈立昂立于风中,一别多年,物是人非。被狱中对头复仇,却偶遇妙手圣者真传,从此叱咤风云,一跃而上!陈立,立于天地之间...
我穿越到了发外夫的世界
你说什么!刘楚楠激动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差点把椅子给带倒了。额。。。先生您先不要激动。刘楚楠对面的身穿白衣制服的美女赶紧做出了阻挡的手势,示意刘楚楠不要激动,先坐下来再说。每一位年满十八岁的男子都有在我们市民服务中心领取一个老婆的权利。刘楚楠穿越到了一个老婆的世界。不用多说了!还等什么!赶紧给我整一我穿越到了外夫的世界...
重生之洪荒圣人
一个山村的少年,意外的重生,使他回到了洪荒时期。他是盘古的兄弟,却又成为了女娲的师弟。圣人与他为敌,那接引准提更是被他用混沌剑劈死了。四处树敌的他将如何面...
全能小神医
农民工江昊,遭女友背叛,被富二代重伤,意外得到修真传承,从此咸鱼大翻身。行医救人,开挂种田,药膳美食,掌掴纨绔富二代,脚踩霸道黑老大,完虐西医,为国争光。...